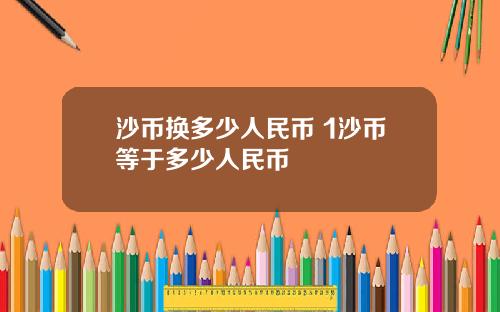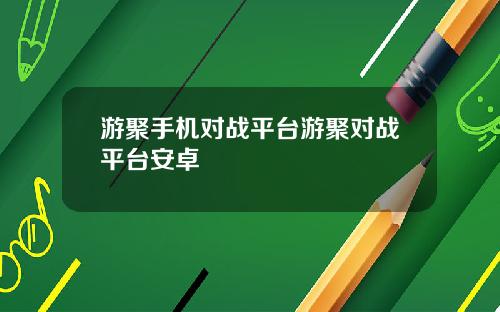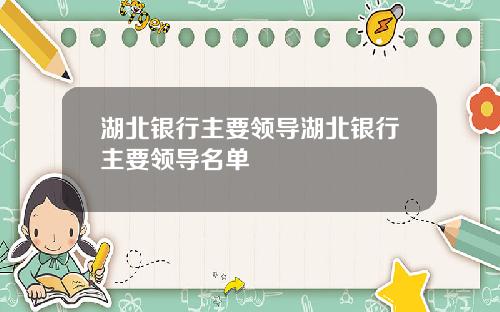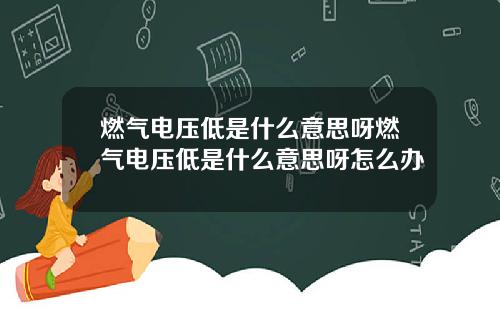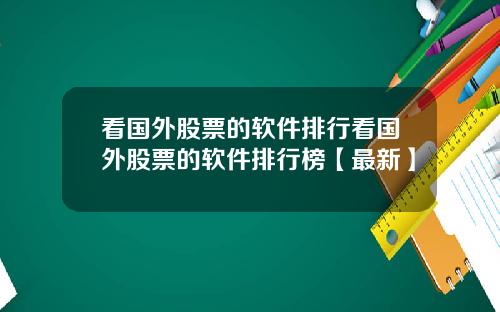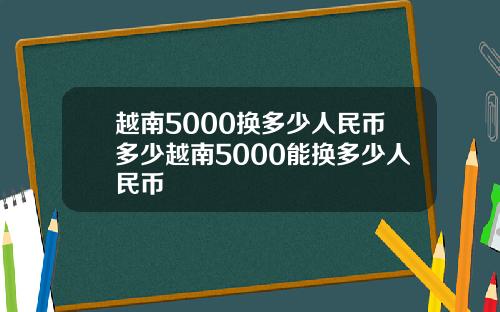文章目录:
1、30年低价理发3万人次 “3元师傅”有把温暖剃刀2、工地里藏着91枚爆炸物……所有人都撤了,只有他在3、“嫖娼被敲诈百万案”涉事官员
30年低价理发3万人次 “3元师傅”有把温暖剃刀
2019-03-20 07:35 | 浙江新闻客户端 | 记者 翁浩浩 通讯员 王艺
3元,意味着什么?或许只够坐两趟公交车,或许只是一笔日常消费的零头。而对朱友才来说,它是一份承诺,更是一份付出的快乐。
今年67岁的朱友才,是温州市洞头区大门镇兰湖洞居委会居民。他和妻子经营一家理发店,普通理发只收3元,对老人和困难群体半价甚至免费,人送外号“3元师傅”。30余年来,夫妻俩低价理发3万余人次,还为临终老人提供上门服务。
因为这把有温度的剃刀,今年,朱友才登上了“浙江好人榜”。
有人说,他实至名归;也有人说,他很普通。日前,记者前往洞头,走近了这位“浙江好人”。
朱友才为客人理发。
海岛最暖的地方
“大家都喜欢他的手艺,有些老人只认他理发。”
大门镇位于洞头区西北部,是当地坐船才能达到的两个乡镇之一。从城区码头出发,约20分钟的船程,就来到了大门岛。
在镇上主干道沙岩街,两边是各类商家,其中不少是理发店,有着时尚的招牌和装饰。沙岩街55号,一处不起眼的老房子,玻璃门上写着“有财理发店”,就是朱友才的店面了。
记者进门看到,店里装修简单,满满的“怀旧风”,镜子前的桌上整齐摆放着电剪、推剪、刮刀、梳子和吹风机等工具。中间有一张“古董式”的铁架理发椅。别看它“岁数”大,360度旋转、90度调节椅背,很受理发者欢迎。旁边有三四个人坐着等理发,大家聊天说笑,不大的屋里热热闹闹。
二月二龙抬头,在这一天理发预示着一年的好运气。理发店的顾客络绎不绝,算下来,朱友才这一天为20余人理了发。
眼前的朱友才个头不高,皮肤黑,目光炯炯,双手干练有力。他手中的推剪在一位老人头上游走,头发有节奏地落下。剪、洗,外加修面,20多分钟就搞定。老人把脸凑近镜子,左看右看:满意!
老人叫朱加权,住在大门镇养老服务中心。把围布掀开的那一刻,记者才发现,他双腿残疾坐着轮椅。老人要付钱,朱友才把手一推:“不用。”随后,他和几位邻里稳稳地把老人抬下门口台阶。老人回头挥手道别。
生活困难的人免费,朱友才的这条“行规”,大门镇上远近皆知。他和他的理发店也成为岛上一道独特的风景。
“他是打着灯笼都不好找的热心人啊!”大门镇养老服务中心原负责人郑祥财说,中心最多时住着20余位老人,现在还有8位,最大86岁,最小61岁,人人认识朱友才。因为每个月朱友才都会骑车上门,边和老人聊天,边理发、刮胡子,“大家都喜欢他的手艺,有些老人只认他理发。”
“以前只听父母说过朱师傅的事,到这里工作后才亲眼看到。”养老服务中心工作人员朱玉英回忆,每年春节、重阳节,朱友才都会来看望老人,有时还带慰问品,和老人们结下了深厚感情。
理发师傅的“执拗”
“我理发更多地是想为大家服务,定下的事可不能变!”
现实生活中,有人通过不同的职业丰富阅历;也有人一辈子从事一份工作,实现人生价值。朱友才属于后者。
朱友才的理发店,是从父辈传承下来的,顾客多是50岁以上的中老年人,其中不少是回头客。大家喜欢叫他“3元师傅”。而朱友才还有另一个昵称叫“刮痧叔”,每年夏天都能大显身手,帮中暑者刮痧。
趁着理发空闲,朱友才和记者聊起了“3元师傅”的来历。
朱友才出生在一个穷苦家庭,兄弟姐妹4人。上世纪50年代,父亲在政府支持下筹办了大门理发合作商店,家境才逐渐转好。每天耳濡目染,朱友才十分钟爱理发这一行当,初中毕业后接过了父亲的剃刀,从此再没放下。
“以前家里很困难,常有好心的亲戚和村民送来大米、番薯干等接济。后来,赶上党和政府的好政策,我们开始自食其力。父亲告诉我,要做个懂得感恩的人。”朱友才说。
感恩二字,融入了他的骨子里。他和妻子决意用手艺回报社会,一直实行最低收费。随着物价上涨,镇上其他理发店价格一次次往上提,可朱友才还是守着3元的老价钱和一如既往周到的服务。
有人说他“傻”,但他不在乎。他说:“我理发更多地是想为大家服务,定下的事可不能变!”
朱友才并不富裕,一家人挤在原先大门理发合作商店的旧房子里,主要收入就是理发。有时一天30余元收入,还不够补贴水电费和其他开支。“这样下去咋行,我们不能让朱师傅自己贴钱!”时间一久,有些老客户也主动提议他涨价。朱友才不答应,他说,子女都自食其力了,他们夫妻吃得很省,也没什么其他开支。
见朱友才来了脾气,这事就搁浅下来。2017年,一位聪明的街坊想了一个折中法子:理发还是3元,其他的如修面等另算钱,总价不超过10元。
“想想大家都是为我好,心里蛮暖的。”朱友才说。新规矩这才施行起来。
一把有温度的剃刀
聊起朱友才的事,没有伟大壮举,却时时感受到戳人心窝的温馨
在理发店一角,单独放着一把电剪,刀头锃亮,上面没有一丝残余的头发。朱友才介绍,这是专门为临终老人理发用的。
大门镇甲山村村民老叶清楚记得,老父亲离世前就是朱友才为他打理的。当时,眼看父亲快不行了,头发没来得及理,他第一个想到的就是朱友才。朱友才刚给几位顾客理完发,正准备歇口气,得知情况后直奔叶家。
那一刻,朱友才也记忆犹新:老人躺在床上,非常安静。他的白发长而乱,显然很久没打理了。朱友才挪到老人身边,微微抬起他的头,轻柔地推动电剪,老人的表情比之前放松一些,静静看着他。朱友才知道,老人是在表达一种情感,他微笑点头。
类似的场景不是一两次。兰湖洞居委会党支部书记朱友贵说,大门农贸市场有一位姓林的摊主,皮肤癌晚期脸上淌污血。家人想让他走得体面些。但一见林某的状况,许多理发师立马回绝,有个理发师甚至开价100元。朱友才听说此事,主动找到林家人:“我来剪,一分钱不要!”
“刚开始有点怕,但我想,总得有人为他理发。”朱友才说,每次替临终老人理发,对方家属给多少钱都不收,非要给钱他还会生气,“只要有需要,路再远、时间再晚我都会去,就是想为老人做点什么。”
这几日,在小岛上,聊起朱友才的事,没有惊心动魄的伟大壮举,却时时感受到暖人心窝的温馨。
第二天上午8时,记者再次来到理发店,生意还没开张,顾客已然上门。不一会儿,只见朱友才骑着小三轮由远而近,车厢里装着冬瓜、青菜、萝卜、包心菜、榨菜等。原来,每天凌晨三四时,他就会到自家的地里耕作,一早把蔬菜拉到店门口,送给有需要的邻里或顾客。
认识朱友才的人,都说他人好。这一点,在理发店里珍藏的一本本荣誉证书里得到了印证——浙江省文明家庭、温州市最美家庭、洞头邻里和谐户、洞头“平安家庭”示范户……荣誉无声,让人肃然起敬。
这就是朱友才。
编后:一座城市的温度来自哪里?来自人间真情。温州的“3元理发师”、衢州的“1元爱心早餐店”、绍兴的“1分钱公益班车”……都让人感受到了一座城市的温暖。这些行动是一个人自我实现的需要,也是整个社会进步的动力。我们欣慰,因为这样的暖心故事就在你我身边;我们也相信,只要大家从自己做起、从小事做起,你一分钱、我一分力,就能燃起更多人心中的真善美,让我们的城市拥有更多的阳光和温暖。
工地里藏着91枚爆炸物……所有人都撤了,只有他在
问
炸弹爆炸后是怎么样的?
——人真的会被气浪推走。
问
反坦克地雷有多重?
——15公斤,相当于一大瓶的桶装水。
问
火药留在身体里是什么感觉?
——就一个字:痒。
回答这些问题的主人公
是浙江省衢州市公安局
特警支队副支队长张建东
一个刚刚被公安部授予
“全国公安系统二级英雄模范”
称号的“拆弹专家”
张建东从龙游排爆现场出来时
上面这3个问题
只是他26年
排爆生涯故事的一部分
接下来
让我们从他的讲述中
感受不一样的世界
我的26年排爆故事
“怕牺牲?就不要当工兵”
“张建东,龙游拆迁工地挖到了铁疙瘩,好像是炮弹……”2016年7月4日一早,特警支队副支队长邱吉庆(现为监管支队政委),敲开我办公室的门,点开一张照片:里面是一片拆迁工地的废墟。我放大仔细看了看,土堆上,好像有几枚不同类型的炮弹、手雷。
“走,去现场!”一个小时后,我们到达龙游县城县学街(原县政府招待所)拆迁工地。废墟附近,竟然还有不少人在围观。中心现场,一个挖了一半的房间墙角,十几枚早期遗留的炸弹,就藏在泥土、碎木板、砖块、树根之间,引信、雷管裸露在外,稍微处置不当,极易引发爆炸。
“警戒线至少拉到100米外!所有人员,必须快速撤出!”
“张建东,里面的炮弹,很危险?”邱吉庆露出一些担忧。
很多没有经历过爆炸的人,也许很难理解:废旧炮弹而已,怕啥?可在1996年进入部队之初,排长就告诉我们,要对“热兵器”有敬畏之心。那时,我还不明白,直到第一次参加新兵训练时——
“什么是工兵?”偌大的训练场上,排长严肃发问。还没等我们回答,耳边就是一声巨响,紧接着远处就冒出一片火光和黑烟。“刚刚爆炸的,是200克的TNT炸药。很危险,这就是工兵!”
那一声巨响和排长的话,现在还常常回荡在我耳际,也开启了我的排爆生涯。正因为知道危险,我必须更了解它。入伍第二年,在全师(工兵专业比武)埋雷(埋、扫、排)比赛中,我获得了多个第一名,并开始担任专业教员,给新兵上专业理论课,成为全团军事技能佼佼者。
可即便如此,意外还是发生了。
1998年,在安徽某个山坳里,正在进行一场“导爆索传爆法”专业比赛。
我们三支参赛队伍同步开展作业,要求每组9个起爆点,一共27个点,同时爆炸。我作为第二组的“点火手”,要在所有人撤离后,点火起爆。按照正常情况,我们3名点火手,有15秒的后撤时间。
“各组听口令,准备点火。点火!”在考官发号施令的那一刻,我就拉掉了“拉火管”,刚要扭转身躯起跑,背后传来“轰”的一声巨响,铺天盖地的灰、泥巴,往脸上砸过来,一股气浪伴随着烟雾,把我“冲”出了几米远,没来得及检查伤势,我就连滚带爬又往前跑了几十米——还有2组起爆点即将爆炸!
爆炸之后,我坐起身,身边都是破碎的石子,周边人一直冲我讲话,可我只见他们嘴巴在动,耳朵里只有“嗡嗡”的轰鸣。往前再一看,原来是1组操作失误,发生了“瞬爆”,点火手的裤脚已经破碎,手上、脸上都是血……
我脑子里响起班长那句话:怕牺牲?就不要当工兵!这一次,我真正开始考虑“牺牲”的问题,也开始对排爆工作,打心底里产生敬畏之心。
“有没有100%的把握?”
“99%!”
“张建东,人员撤离完毕,做好准备,按计划前往中心区排爆。”邱吉庆的话,把我拉回龙游现场。这天中午,中心区域只剩下我一个人,陪伴我的是“老朋友”——几个爆炸物转移专用箱。
龙游排爆现场
按照我之前做的转移方案,十几枚爆炸物,3小时应该足够了。可当我拿着工兵铲,一点点铲开泥土时,20式82毫米迫击炮弹、各式榴弹、M24型手榴弹、日军的91式手雷……一个个“显露真身”时,我意识到不对劲:这极有可能是一个老“军火库”!
这其中的品类之丰富,让我都大吃一惊。要知道,在部队我排除过各类军用未爆弹药,我经手过的爆炸物有近千枚,在参加公安工作后,也排除过一些遗留的爆炸物。可“军火库”里,竟然还保存着一些只在资料上见过的品种。比如马尾雷,这是一种手雷,有一根像马尾巴一样的绳子,它是给骑兵用的,在手上抡上几圈,就可以丢得很远,在抗日战争时,用得比较多。
那天,虽然才7月初,可太阳很烈。穿着排爆服的我,早已被汗水湿透。但我没觉得累,也没觉得枯燥,那些资料上才能见识到的炸弹,真实出现在眼前时,我有一种不亚于挖出“文物”的兴奋感。
随着天色越来越暗,我陷入地面越来越深。那个坑的深度,也从小腿肚被我挖到了齐腰深。爆炸物,也已经多达50多枚。看样子,底下可能还有不少。
“今天可能挖不完了,天太黑,有点危险。”从中心现场出来后,我们安排了警力在警戒线外值守。万一有老百姓误闯,那可就太危险了。
第二天早上8点多,我再次到达现场。原本风平浪静的排爆工作,在早上9点多,发生了转折——
在排除几颗堆积在一起的手雷时,我突然触碰到一块铸铁。这不是普通炸弹使用的材质!等我用手拨出它的全貌,不知是热汗还是冷汗,从脸上滴进了土里。
一枚反坦克地雷!
这是我第一次见到这种类型的地雷。资料介绍,这是解放前的地雷,圆形,因是铸铁的约有10几公斤重,40厘米左右直径,上面有2个木把手,侧边上有引信,可将坦克炸个洞。
它有多厉害?打个比方,如果手雷炸了,我能留全尸;可地雷爆炸,就只能找“碎片”。
我再次走出中心圈,请示当时赶来现场的时任特警支队支队长胡伟民。
“你有没有把握,100%能安全转移?”
“100%不敢保证,只敢保证99%。”
“张建东,举起手来”
剩下的1%,不是我对专业的不自信,而是现实。排爆没有100%的成功率,意外随时会发生。毕竟,我也曾拆“爆”过。
2014年,江山收缴了一批爆炸物,是5个土制炸弹,需要进行鉴定。作为衢州市反恐专家人才库唯一的“排爆专家”,我接下了这个任务。
到现场后,我们对土制炸弹进行了分析,它直径3厘米,长5厘米。虽然只有大约一个指节大小,可它并不好拆,里面的爆炸装置,只要发生一点点摩擦,就容易爆。我们选择在废弃篮球场拆解,室内只留下当时的排爆大队教导员周磊,进行拍摄。
我将炸弹放在地上拆解,以此减少“万一”爆炸的面积。1个、2个……顺利进行到第3个时,炸药只剩下指甲盖一点,“分离大块一点行不行?”
有时候,手的动作总是比脑子转得快,这个念头还没过完,就是一阵刺痛。我左手握着的钳子,突然弹飞半空后,出现在我眼前;紧接着就是弥漫开的白烟和火药味,以及一声闷闷的“鞭炮响声”——
很快,我反应过来,“完了,真拆爆了!”
我虽热还是跪坐着,但上半身被冲击,后仰倒在地上。我不敢去看四周以及我的手,我根本感知不到它,它还在吗?我们见过很多排爆专家,手没了,甚至命也没了……
“张建东!你把手举起来,给我们看一下!”周磊低沉的嗓音,在篮球馆回荡,也打断了我的思绪。我缓缓坐起身,机械地向上举起手。
“手还在,还在!张建东,你看看!”四周脚步声包围过来。我低头看了看血肉模糊的手,黑色炸药和碎石子都嵌进皮肤里,变成一个个“麻点”。那一刻,我有点想哭,不是因为疼,那早已疼麻了,而是我保留下来的双手,还能继续我热爱的事业。
那晚回家,妻子第一次哭了,也是第一次骂我自私,“你有没有想过,除了你的事业,你还有家庭?”每天,只要我不回家,客厅的灯一定亮着,她说这是平安灯,“希望你每天都能平平安安回家。”
火药,因为清理不干净,就这样留在了虎口。会痒,特别到了夏天,更是痒到发狂。在那之后的3年里,炸药探测仪,只要放在我的手上,就会发出警报。
每次,虎口痒的时候,我就会提醒自己:“小心,再小心!”
回到龙游现场排爆的这一天,当我面对那枚“反坦克地雷”,反复告诫自己:再慢一点,再稳一点……1个多小时后,当我浑身湿透怀抱着手雷,走出中心圈时,大家用一个个大拇指迎接着我。
那天中午,当现场全部清理干净,我们一数,足足清理、转移出91枚、20多种爆炸物品。这一次任务,顺利完成!而那短短2天,我足足轻了1.5公斤。
这么危险的活儿,为什么一干就是这么多年?
“拆弹不是谁都能做的,需要上天的批准。”《拆弹专家》的电影里这么描述排爆手,那么,既然被上天选中,我,又有什么理由退缩?
——张建东
转自浙江法制报
来源: 中国警察网
“嫖娼被敲诈百万案”涉事官员
6月19日,中国纪检监察报刊发《放纵欲望种下“毒瘤”》一文,披露了浙江省常山县人民政府原党组成员、副县长顾建华的问题。
此前,中国裁判文书网于今年4月公开的俞欧、汪丽俊、黄慧忠等敲诈勒索罪一审刑事判决书,曾披露官员嫖娼被索百万案,常山县三位县领导2011年嫖娼被抓后,遭派出所驾驶员俞欧等人敲诈勒索100多万元。
顾建华即为三位嫖娼被抓的常山县领导之一,时任常山县环保局局长,另两位县领导分别是时任常山县副县长甘土木,时任常山县人大常委会副主任熊雨土。
据判决书,熊雨土称,2014年4月27日下午,他和王某(浙江鸿宇生物科技有限公司、衢州三达交通建设工程有限公司负责人)开车到杭州,找顾建华、甘土木玩,“晚上四个人每人叫了一个小姐并发生了性关系,之后就被杭州市下城区武林派出所当场抓获。在接受处理的过程中,当时派出所的一个协警小俞(即时任派出所驾驶员俞欧)帮忙,把其几人真实身份隐瞒了,并得到了从轻处理罚款500元”。
俞欧称,得知三位县领导嫖娼被抓,他就到派出所办案区见到顾建华,顾建华叫他帮忙疏通关系。这之后,他欠了高利贷无力偿还,就想起县领导嫖娼被抓的事情可以敲诈些钱,打电话给顾建华约见面。见面后,他提出要50万。三人说上班的人拿不出来这么多,后来顾建华把王某叫来,谈好30万元处理这个事情。此后,他又以相同理由,数次敲诈顾建华等人,一共拿到78万元。
继俞欧之后,顾建华等三人又被汪丽俊、黄慧忠和丁建国敲诈。
汪丽俊供述,他2013年听人说县政府大楼通下水道的时候发现领导办公室厕所下面被避孕套堵了,就翻到县领导通讯录,看到副县长顾建华,就打个电话想试试顾建华是否有什么事情“蒙”他一下。“你在外面干了好事”,在电话里他跟顾建华说;顾建华压低声音说“都是几年前的事情,是分局搞我们的”,之后顾说有事留个电话就挂了电话。
他把这次通话,告诉了舅舅黄慧忠。黄慧忠办了一张金华的号码和手机,让他打电话给顾建华。一个不是顾建华的号码和他联系,问他想怎么解决,他提出要100万元也不为过,双方讨价还价到20万,他最后共计拿到了16万。
判决书中有顾建华的证言,证实在2013年10月接到一个衢州的电话,说知道几个领导在杭州嫖娼的事情,“对方后来经常用一个金华号码打来威胁要去纪委举报,刚开始对方要几百万,后来一直在讨价还价,是叫王某去联系(汪丽俊)的”。
丁建国是从安徽老乡处得知顾建华等三人嫖娼被抓的事情,他专门办理了一张杭州地区的号码,并虚构“杭州武林派出所大哥”身份,向顾建华等人索要钱财,否则就向纪委举报。判决书称,为了稳住丁建国,顾建华等人经商议,决定由王某提供工程项目给丁建国承建,丁建国最终获取43万元工程款项,并敲诈了8.7万元。
顾建华、甘土木、熊雨土等三人已经分别在去年六月、七月被“双开”并移送司法机关。其中,去年12月,顾建华因犯犯受贿罪,被判处有期徒刑4年,并处罚金33万元。
“没有哪棵树生来就是病树,没有哪个干部注定走入迷途。顾建华亦是如此”,中国纪检监察报19日刊发《放纵欲望种下“毒瘤”》一文谈到,顾建华1964年出生在一个基层干部家庭,18岁参军,21岁成为国家干部,23岁入党。“2000年初,36岁的顾建华担任常山县狮子口乡党委书记,干劲儿十足的他结合自身优势,短期内使全乡各项工作走在全县各乡镇前列。此时,他恰有一篇署名文章在省级媒体刊发,在全县颇具影响力,可谓是春风得意”。
可之后,“一次意料之外的干部任命,竟成他思想的重要转折点”。2001年,常山县部分乡镇区划调整,顾建华所在的狮子口乡和天马镇合并,他被任命为偏远山区芳村镇党委书记。“这一任命显然背离了他的预期”。
“顿时感觉自己受到了不公正对待。”顾建华回忆说,原本信心满满的他倍感失落,对组织的不满油然而生。尽管在家人和同事的劝慰下,他如期赴任,但心存不满,只有一个目标,那就是早日离开艰苦环境,尽快调到好单位享清福。自此,他开始了自己的“两面”人生:表面上看起来仍是名“狮子型”干部,端着做事风风火火、雷厉风行的姿态;实际上却隐藏着一颗扭曲的心,贪图享乐、追求奢靡。
审查调查人员介绍说,“八小时内”,顾建华极力塑造自己的“良好”形象,一心扑在工作上的“工作狂”,亲近企业的好领导,廉洁奉公、嫉恶如仇的好干部。但“八小时外”,他混迹于“圈子”之内,已然找不到自我。
“常与所谓的同路人‘同流’。晚上吃饭、唱歌、夜宵接续进行,醉生梦死,乐此不疲,”在接受审查调查时,顾建华坦言,面对妻子的规劝,他不是虚心接受,而是怒目以对。第二天上班云里雾里,闭目养神,以备晚上再战。“用今天的眼光审视当时的我,‘四风’问题除文山会海不沾外,其余具体表现在我身上都有,而且很突出。特别是铺张浪费、挥霍无度、骄奢淫逸等奢靡之风,像是为我精准画像。”
文中谈到,“放任不良作风之后,顾建华对金钱越来越渴求,从不想收、不敢收,慢慢转化成有选择性地收。”他把手伸向了分管的工程项目。2014年下半年,常山县计划实施城区道路亮化节能改造工程,分管该项目的他提前向某公司负责人陈某某透露相关消息,并表示可以提供后续帮助。
2015年初,顾建华收受陈某某的“感谢费”6万元。同年11月,陈某某得知顾建华陪妻子到上海看病,为了能得到顾建华的持续关照和支持,随后赶赴上海,帮他忙前跑后、送礼办事。
与一些人不同的是,顾建华受贿大多在办公室,不敢让家人尤其是妻子知道。“在乔迁新居、女儿结婚等节点,顾建华的妻子得知有老板给他送红包,都会原数甚至加倍退回。”审查调查人员说。
但妻子的行为也未能阻止顾建华深陷泥潭。如今,高墙之内的顾建华悔不当初。“我真的不该走到这一步!”面对审查调查人员,顾建华情难自抑,失声痛哭。
新京报记者 王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