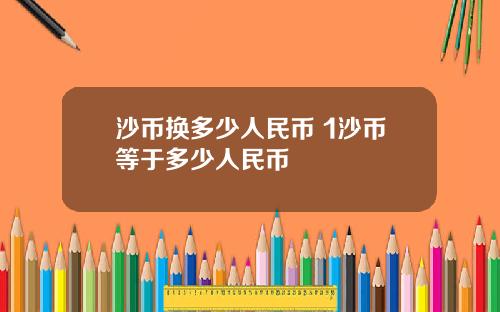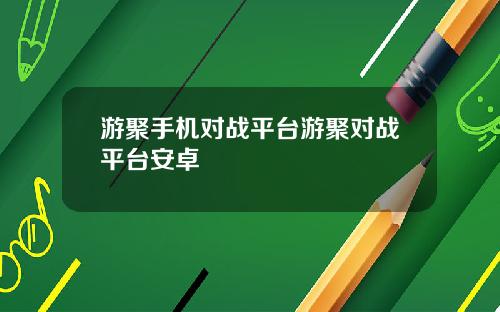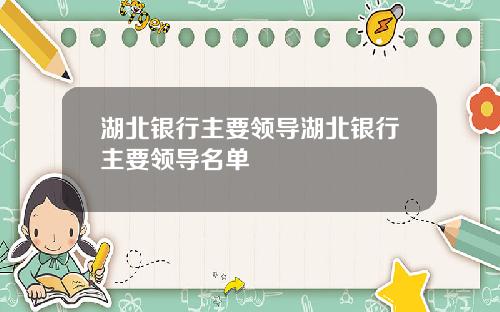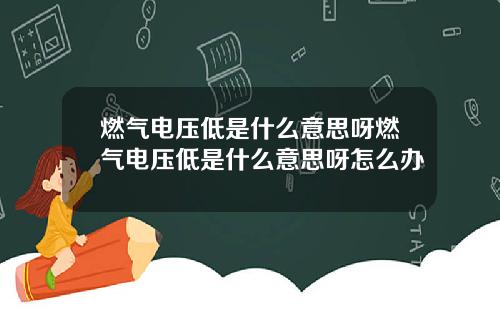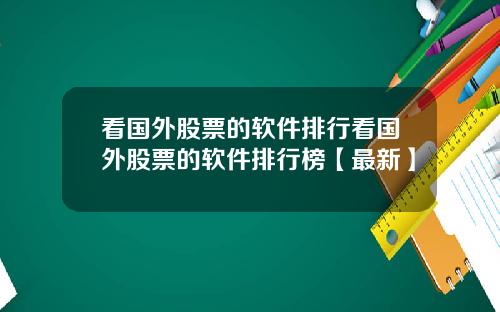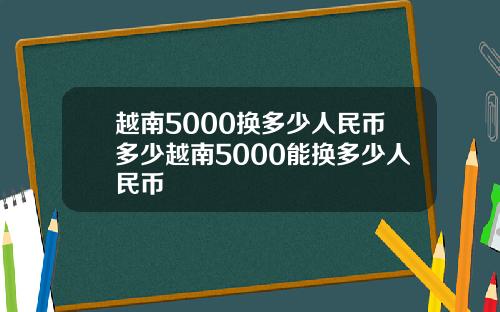公益慈善领域最大的“本钱”是人,高校公益慈善教育需要从国家人才战略、学科建设、人才培养、就业市场、资金支持等方面实现突破。期望通过高校和公益行业的共同努力,促进公益慈善教育的发展。
主笔:歪眼镜
“你们缺人吗?”对于一部分中国公益机构的负责人来说,这个问题都被视为“题面即谜面”。
“缺人啊,我们的基金会不知道为啥,这么招还是缺人”,某地产企业社会责任项目负责人感慨,“即便是我们这种工资待遇还不错的企业基金会”。
这位从公益机构跳出来的负责人将目光转向“老雇主”,先后挖了许多位“老朋友”和“老朋友的朋友”,才堪堪补上缺人的窟窿。
“老雇主”也要补些“新血液”,问题随之而来:去哪招人?工资不够吸引人怎么办?“我喜欢的不喜欢我,喜欢我的我不想要”......
人才之困
带着小红帽,拿着扫帚或小红旗,在敬老院、幼儿园和老旧社区清扫后展开旗子合影,一场“公益活动”“圆满”结束。
曾担任某高校团委副书记的邹敏如此形容其所在学校的公益行动,“这几乎是这所学校有关学生最大的公益活动,无论是从参与人数,还是学校态度”。
邹敏一边打趣,一边播放手机里收藏的短视频。视频中,路上的环卫工人正忙着清扫街道,破旧的制服上挂着冰碴,道路的另一侧,几位身着红色马甲、戴着袖箍的女士每人手上拿着一把小扫帚拍合影。
“跟这个很像,我的学生们当时忙得最重要的事情就是合影。”邹敏指着手机有些愤怒,“当时也不知道领导在想什么,竟然让每个班都开一个微博,做一次‘志愿服务’就发一条微博,内容就是今天去了哪里,配上9张照片。”
而这样的动作还不得不做。据邹敏介绍,这样的志愿服务被数据化为“志愿小时数”,与“评优评奖”(指评定奖学金、学生荣誉、入党积极分子等)直接挂钩。
后来,一些学生的讨论传到邹敏耳朵里,内容多是学生们对“作秀”的不屑和怀疑,以及临近“评优评奖”前的突击行动。
保定学院经济管理学院实习实训办公室主任陶龙渤也观察到这样的现象,并对这种现象带来的后果表示深深的担忧。
“如果学生不再相信善,而将本意是培养善的教育行为当做‘作秀’,结果不堪设想”,陶龙渤坦言,“尚且不论培养公益行业的专业人才,仅是培养这个社会的普通公民,都非常不合格。”
他将原因归之为一个字——“懒”。
“制定政策的老师懒得去了解公益理念通识培养的价值,执行政策的老师懒得学习更多的知识,采取更科学的手段。”
在他看来,专业、科学的公益通识教育至关重要:一方面有助于培养公益行业稀缺的复合型人才,另一方面则基于更宏观的社会发展,“在物欲横流的今天,公益通识教育是社会道德建设的有效手段。”
清华-敦和中国高校公益慈善教育发展论坛
“我们现在其实特别缺少一些复合人才”,在日前举办的首届“清华-敦和中国高校公益慈善教育发展论坛”(以下简称“论坛”)上,腾讯公益基金会秘书长葛燄表示,“我们可以找到非常有公益精神的人,在整个公益行业可能服务了很久,但是商业思路,尤其是对于互联网技术的理解还差得很远。”
这句话的背后,是共同富裕理念不断推进的今天,企业对具有公益理念的复合型人才,十分迫切的需求。
葛燄介绍到,“我几乎每天都在看人、招人。在这个过程中,发现其实在这个行业里特别缺少一些复合人才”。她举例说道,具有公益理念的科学家可以开发出自闭症儿童早期筛查的软件,通过等距的摄像头捕捉孩子看到不同图案的眼神,AI识别有多少可能性是自闭症。
“人才实际上是一个泛的问题,哪都缺人才,即便再成熟的商业也缺人才,公益慈善领域更甭说了”,北京大学法学院副教授、北京大学非营利组织法研究中心主任金锦萍进一步表示。
南都公益基金会名誉理事长徐永光则将这种人才短缺情况进行了描述,与文首所说的状况相印证。“现在我们面临什么样的人才困境?我觉得有两个非常显著的特点”,徐永光总结:“第一个是吸引不了人,第二个是找不到人。”
他解释道,前者是行业共识,而后者则直接导致公益行业薪酬拉高,“因为没有,也没有竞争,就是挖人、挖墙脚。”徐永光认为这是正面信号,“这个行业要人、缺人,你们来了,来了以后可以有饭吃,会吸引好多人进入我们的公益慈善行业。”
不过邹敏对此颇不认同,“目前行业还是缺人,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就是薪酬同比太少。”
对于这一点,不同人因所处环境不同,感受也并不相同。但大部分从业者都有一个共识:需要培养更多懂公益的人才。
大学之育
如何培养公益人才?大学作为核心环节和主要平台至关重要。
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教授、清华大学公益慈善研究院院长王名认为,大学公益教育具有其使命,在于“省方、观民、设教”,亦在于“明德、亲民、止于至善”。这种使命是对“美好人生、美好大学、美好社会”这三维愿景的直观映射。
他将省方概括为“建构理论,传承道孔,以学术影响政治、制度和政策”,并认为“这是当下中国致力于公益教育最能够发挥影响力的一个方面。”
在他看来,一方面是要帮助那些需要帮助的人,并努力提高他们的生命价值,以达务民之义的社会意义;同时也在于提高每一个公益教育和公益实践当事人的生命价值,以上敬天地对得起祖先和不辜负良知,同时要远离各种恶,“敬鬼神而远之”。
但对于当前中国高校公益慈善教育的现状,多位专家表示并不乐观,“我们当下更多关注商业慈善,对于慈善教育关注不多”,上海财经大学商学院教授刘志阳认为,“输血式的救济包括商业的扶贫行动不足以改变未来的社会,慈善教育是更为根本的造血式行动。”
徐永光则认为,中国高校的公益慈善教育不只是不足,而是“零”的突破,其中一个重要的原因便是“本科教育的突破”。
“第三次分配成为基础性制度安排,所以一定会大大推动第三次分配,这样人才马上就更加捉襟见肘”,徐永光表示,“高校要搞学科,国家人才战略是第一。”
谈到目前大学教育面临的问题,中国红十字基金会副理事长、红十字国际学院副院长王汝鹏说道,“第一是师资,现在慈善教育、人道教育师资奇缺。第二是教材,把讲座当教学,把课件当教材”。
金锦萍则表示,“高校的慈善教育需要哪些资源?可以说什么都缺,但是什么都缺就意味着这个问题上我们有极大地提升空间。”
黄浩明将这些问题总结为动机动力问题,认为当前我国高校在公益慈善教育上面临的主要问题集中在四个动力机制上:共同体、互益、共赢和加持。
他以日本社会组织发展状况举例,“日本有很多非营利性组织的领导由高校老师兼任”,来自教育本身的影响补充了公益项目对专业人才的需求,甚至影响更多学生成为潜在捐赠人。
而如何确保公益的大学之育能够向前推进,徐永光等一众专家的观点里都认为少不了资源上的支撑。
“慈善这个事情绝对不是非营利组织自己一家的事,也绝对不是公共管理学院一家的事,恰恰它是所有人都应该参与的事”,刘志阳说道。
王汝鹏也表示,“人道教育和慈善教育要建立共同体,在师资、课程、教材、基础设施等各个方面要实现资源共享。”
在保证大学公益之育能正常进行后,更多的思考则聚焦在人的身上。
浙江敦和慈善基金会项目经理叶珍珍从公益机构的角度延伸思考,并设问:公益慈善教育在培养什么样的人?怎么样去培养?为谁来培养?
在这一视角中,叶珍珍将思考落地在人才需求和高校教育的平衡上,并将之比喻为“翘翘板”。在她看来,高校有自己的理论体系、价值体系和知识体系,有其目标和标准,进而形成模式,而翘翘板的另一端,则关注人才自身的需求和发展。
根据墨德瑞特新近发布的《中国公益人才能力发展趋势2021》数据观察显示:在公益人模型中,向往美好社会是工作动力之一,但系统思考能力亟需提升,而这恰是公益慈善通识教育所能补充的内容。
通识之教
“从基础来讲,我不知道我们这样的二本院校未来会不会在这方面有所发展”,陶龙渤坦言,“目前能做到的就是推动公益慈善文化渗透进更多孩子们的心里。”
在深思之后,陶龙渤决定开设名为《公益与志愿服务》的通识教育课程。
在开设一学期后,陶龙渤不再纠结于“公益”与“志愿服务”的区别、关系、渊源,甚至拿掉了很多课程设计之初要讲授的理论知识。
“我得做件事情,让这些孩子知道,公益到底是什么?与我们生活有何种关系?”他笑着说道,“我得让孩子们长长见识,让他们在上完课的一刻觉得,公益还能这么做!”
张璐瑶便是应陶龙渤之约,担任《公益与志愿服务》通识教育课程的校外老师,每学期都会结合自身项目经验讲授实际项目执行经验。除了张璐瑶,接受陶龙渤邀约的还有公益媒体记者、公益领域学者、一线社会工作者和政府主管部门工作人员等。
但在这一年里,他也发现一些问题。“过于实践导致课程不成体系”,这是他单打独斗必然面临的结果,“因为重视程度不同,我只能依靠自身的社会资源弥补不足,吊着一口气,确保这堂课能一直开展下去”。
南开大学周恩来政府管理学院教授朱健刚在研究中也发现了这个问题,认为高校公益慈善教育从学科基础角度出发,不能仅看应用学科,还要关注到最基本的一些学科脉络和理论。
“教育的学科基础还是要有相关研究,既需要经验研究,也需要理论研究”,朱健刚表示,“我不希望公益慈善教育好像只是应用的,(只考虑)怎么满足职业人才的需要。”在他看来,满足需要的同时,也需要考虑平衡,高校公益慈善教育应对整个实务界产生引领、反思、批判的作用。
复旦大学通识教育核心课程委员会副主任李宏图也认为,“对于慈善教育而言,我们有一个务实性的导向,还是着重于理念的教育。”
他进一步解释,作为双一流大学,复旦大学学生的培养目标便是“要在多个学科当中认识世界、理解世界以及确立并提升他的能力”,因此不能狭隘地理解慈善教育,需要进一步扩展开来,与福利社会、现代社会等内容结合,“当然也需要理论性跟实践性相结合”。
除了在通识教育的理论性与事务性研讨之外,参加论坛的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教授、清华大学公益慈善研究院院长王名则将目光聚焦在高校公益慈善通识教育的实现路径之上。
王名认为,这样的路径有两个:其一,如朱建刚所讲的公益社会学思路,学科发展或学科建设可以跟成熟的学科去结合,借助已有学科来建构一个新的学科体系;并由此引出更多的可能,如公益经济学、公益法学、公益管理学等。其二则是学群、板块的方式,如将公益慈善打散成类似社工、慈善等几个不同的板块,每个板块都可以建立学群,围绕实践的需要来组建不同的学群。
8日傍晚的选修课,陶龙渤对着教室里不到一百位的学生有些感怀。看了论坛上发布的报告,他既乐观,又无奈。乐观于不远的将来可能会实现他的夙愿,无奈之处则在于,当前的他仍是孤军奋斗。
“同学们,我想掏心窝子说一句,这社会还有很多问题,残障、罕见病、孤独症、教育不均衡等等,你们不一定以后会从事公益行业,但请你们记得,要永远善良,多行好事。”
(刘嘉琳对本文亦有贡献)